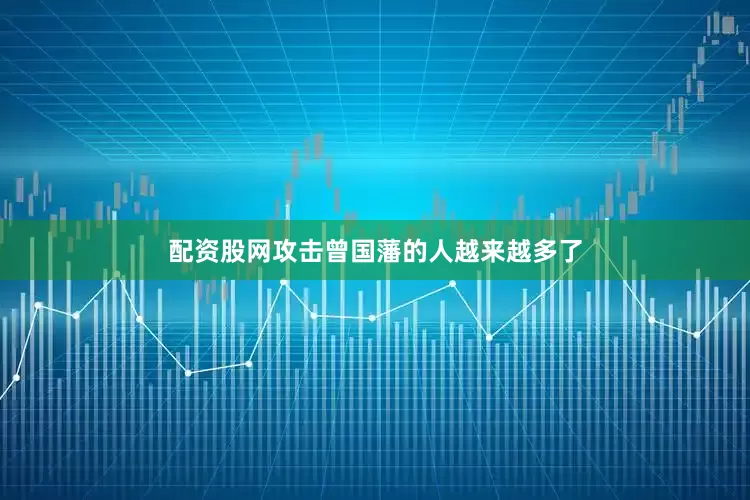
早在湘军的炮火把天京城墙轰塌之前,洪秀全的理想就已经破灭了。
在太平天国的旗帜之下,成千上万的小生产者,信仰着西方的上帝,企图挽救世道人心,向传统宣战。但若仔细剖析他们脑中的想法,也许只能得到一团混沌:白莲教的末世观,民间的降僮术,江湖义气,小农的平均主义,皇帝梦……驳杂而又矛盾。
另一边,太平天国的掘墓人——曾国藩身后的儒生和农民,追随着一个古老的理想。
在太平军的冲击之下,曾国藩看到了末日景象:“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他未必多么忠心于清朝,毕竟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尺度里,王朝更替实在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但即便夷狄入主中原,也要祭拜孔子;李自成之流再穷凶极恶,都“不犯圣庙”;而洪秀全偏偏执着于摧毁偶像,置圣道于不顾。
于是,在《讨粤匪檄》中,曾国藩说:“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这份捍卫传统的信念,引发了那个时代最暴戾的杀机。

1
1853年春天,两湖局势糜烂,皇帝下令在家守孝的曾国藩管理湖南的团练。
曾国藩深知绿营病入膏肓,即便孔子复生,三年之内也不能革除旧弊。他决定另练新军,“决不用营兵,不用镇将”。他任用饱读诗书的儒生为军官,招募朴实勇敢的山地农民,“但求其精,不求其多”。并且要求军官必须亲自招募下属,与部下共同进退。军官与士兵,就像是家族里的父与子。军官御下,如父管子,不得溺爱;士兵事上,如子事父,不得忤逆。
这种书生气放到练兵上意外的有效。一来,流氓无赖进不了军队。二来,将官对士卒知根知底,士卒不容易临阵脱逃。
湘军成军的第一个阻碍不是敌人,而是地方的山头主义。当时,清朝一共委任了289位在籍绅士办团练,没给他们任何名号,也没有说明他们拥有哪些权力。办团练涉及治安、征税、司法等问题,必然导致一省之内,政出于二,埋下争权的隐患。这是统治者惯有的小心思:一方面希望变革,以应对时局;另一方面又害怕变得太多,把自己变没了。可以说,曾国藩从来都没有得到朝廷的信任。
那段时间,曾国藩除了练兵,还致力于清剿土匪,不时越过州县衙门,在其公馆内的审案局处置罪犯。他认为,湖南匪患严重的根源在于地方官姑息养奸,“积十数年应办不办之案”,“积十数年应杀未杀之人”。他决定乱世用重典。凡是到了审案局,能完整出来的很少,宁肯错杀,不可少杀。从此,他便有了“曾剃头”的名号。
曾国藩从不在意自己的双手沾满鲜血。杀“土匪”时,他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后来杀太平军时,他说:“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术已自不慎。”
轻描淡写间,说出最残酷的话。人头滚滚而下,内心不起波澜。在他眼里,孔孟之道,亦是杀人流血之道。
湖南的州县官并不关心冤不冤案,只在乎权力少了多少、政绩好不好看。查出这么多“土匪”,杀了这么多人,功劳全是曾国藩的,他们却要背个“治理不善”的锅。于是,攻击曾国藩的人越来越多了。
进入夏天,湖南官场的空气愈发炽热,曾国藩不由得感到束手束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官不绅”。有点实权,没有名分,如何施展拳脚?
即便如此,他仍不愿放松一二。
湘军这边,他从绿营借调来一员猛将——塔齐布,此人治军严明,训练有方。湘军日日苦练,引起了绿营高级将领的不满。长沙协副将清德说,塔齐布谄媚曾国藩、败坏军队;湖南提督鲍起豹说,盛夏操练是虐待士兵,下令各营停止操练。曾国藩知道自己的尴尬处境,又不可能向上索要官职,只能连上两折,保塔齐布,弹劾清德。
此举进一步激起了绿营对湘军的仇视。清德被革职后,绿营士兵常来殴打辱骂湘军,只要湘军动了手,鲍起豹就要抓人,曾国藩也保不住自己的部下。某日,一个湘军士兵试枪时误伤绿营的一个勤务兵,绿营执旗吹号,操起火器,找湘军开仗。曾国藩自知理亏,只能交出那名士兵。那名士兵被打了两百军棍,而闹事的绿营士兵没受一丁点惩罚。
不久,绿营兵又来找湘军麻烦,曾国藩要求逮捕闹事者。鲍起豹将该兵士缚于辕门,任凭发落。曾国藩本打算杀人立威,但绿营兵纷纷上街哄闹,导致局面失控。有人冲进参将署,欲杀塔齐布,塔齐布躲进菜园,才得幸免。湖南文武官员均不过问此事,冷眼看着曾国藩的笑话。绿营士兵愈发猖狂,竟然冲入了曾国藩的办公室,打人砸物。最后,曾国藩向隔壁的湖南巡抚骆秉章求救,骆秉章才出面将乱兵赶走。
此事之后,曾国藩自知省城官场容不下他,带着部队灰溜溜地去了衡阳。在那里,他可以专注练兵,不用与绿营争长短,也没有官员的掣肘。湘军立刻扩员数万人,还有了水师,形成了一等一的战力。统领水师的两位将领——杨载福和彭玉麟,于微末之时受曾国藩提拔,对其十分忠心。日后曾国藩屡受打压,仍可复起,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只有他能协调这支纵横长江的水师。

1854年,曾国藩率军出征。他虽练成了一支强军,但在统兵作战方面堪称外行。那年春天,湘军进至岳阳,却迎来了一连串惨败,被迫退回长沙。随后,太平军占据了靖港和湘潭,对长沙呈夹击之势。曾国藩派出主力进攻湘潭,自己则率一支四十艘的舰队往北,欲夺回靖港。湘军在上游,本有顺风顺水之便,但士兵经验不足,舰队冲的太快,直接闯入太平军的射程中,挨了一顿炮击。随后,太平军派出一百多艘小船,分头围攻湘军大船,湘军不敌,纷纷弃船上岸。曾国藩听说水军失利,立马派遣陆军增援,结果一战即溃。他执剑督战,也不能遏止败势。
从练兵之初,曾国藩心里的弦就一直紧绷着,如今遭此大败,愤怒羞愧交集,心理承受不住,一跺脚,跳了湘江。幸亏幕僚搭救,才捡回一条命。执念越深的人,越不吝惜性命。为了大局,可以牺牲成百上千条人命,当事不可为之时,又可以决然舍弃自己的生命。
上岸之后,曾国藩依然打算寻死。这时,好友左宗棠从长沙过来,看到他垂头丧气的样子,说道:“事尚可为,速死非义。”
在对抗太平军这些年里,曾国藩不知写了多少封遗书,不知动了多少次自杀的念头。击溃他的,和支撑他最终挺下来的,是同一个东西:“大义”。
随后,湘潭传来捷报,湘军大胜,曾国藩可以不用死了。
1854年整个夏秋,湘军将太平军赶出了湖南,夺回了湖北的省城武昌。一连串的胜利让长沙的官员闭了嘴,却让北京的大人犯了难。咸丰帝知道湘军夺回武昌,龙心大悦,说道:“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然而,大学士祁寯藻说了一句:“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
此时,曾国藩行走官场的身份证是“前礼部侍郎”,湘军也是自成一体的武装,并非正规军。清廷要容纳他们,意味着重大体制之变,不仅麻烦,还有可能被取而代之。皇帝可以放权,却迟迟不肯授权。

2
曾国藩的部队并不是唯一打胜仗的湖南军队。自太平军过境以来,湖南各地成军无数,从这点上说,曾国藩更像是湘军里的方面大员。至于发动湖南这台战争机器的人,非左宗棠和骆秉章二人莫属。
骆秉章与洪秀全同为广东花县人,身在他乡,要想事业有起色,必须借重当地人。洪秀全倚赖杨秀清、萧朝贵,骆秉章也需要左宗棠。史载,“骆秉章应变审机,不动声色,湘阴举人左宗棠佐之调度,悉合机宜”。两人筹集粮食,将一波又一波湘军送出省外,“南防粤寇,北御鄂氛,西堵黔边,东防江右”。以一省之力,防五省之寇,还能助剿太平军。
湖南本非富庶之地,如何能支持这样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户部指望不上,皇帝直接下令各省就地筹饷。曾国藩试过募捐的法子,求了不少人,卖了不少官,后来发展成了勒捐,也杀了不少人,所获颇丰——这个办法虽然有效,毕竟不能当作常态。各地的有识之士纷纷把目光看向田赋之外的税收,主要是“厘金”(一种商业税)。
户部既然下放财权,那便不用旧章了。左宗棠设立新局,用的不是衙门里的人,而是地方绅士。这些人想进来,少不了保举和捐输,可谓是一举三得。一来,得到了钱财;二来,进来的人能办事,更新了官员队伍;三来,不与旧衙门产生纠葛,避免了因循之风。唯一的输家恐怕就是州县的书吏幕僚。
近代意义上的“地方财政”出现了,旧官员被会搞钱的新官员取代了。正如横空出世的湘军一样,这些人只差朝廷的正式授权,就能形成新的权力中心。
崛起的新势力之间并非一团和气。骆秉章与曾国藩之间就颇有恩怨。曾国藩在长沙练兵时,曾有两个志同道合的伙伴,罗泽南和王錱。王錱能力很强,但锐气太盛,不服管。曾国藩多次告诫他不要贪多,少募一些兵勇,以免陷于无饷可发的困境。王錱不听,反而联系上了骆秉章。之后,曾国藩忍无可忍,要裁撤王錱的部队,骆秉章不同意,保下这支军队。这就是所谓的“老湘营”,后来一直归左宗棠调遣。

1854年,湘军攻下武昌。那时,剿灭太平军主力的担子主要在江北、江南两大营身上,湘军的任务就是夺回长江沿岸的重要城市。曾国藩率军顺江而下,进入江西。那年冬天,他集结兵力,准备攻下九江城。1855年1月,太平军利用湘军急于求成的心理,将其100多艘战船引入鄱阳湖,再将其水师分成两截,逐个击破。看着战船被毁,曾国藩气血攻心,打算骑马冲进敌营,一死了之。部下连忙将其拉回,阻止了他的第二次自杀。
这场大败之后,曾国藩困守江西,如同漂泊无依的一叶孤舟。他没有地方的实职,不好在江西抽取厘金,很难筹集到粮饷。江西官员一如湖南官员鄙视他、抵制他、嘲笑他,使曾国藩备感羞辱。湘军本身是跨境作战,并非保卫家乡,如今又吃不饱饭,哪里会有斗志?
另一支湘军的命运则完全不同。1855年2月,太平军再入湖北,兵临武昌城下。曾国藩派遣时任湖北按察使胡林翼率兵勇一千八百人及外江水师回援武昌。胡林翼不敢与太平军硬碰硬,便驻扎城外,伺机而动。武昌被轻松攻占。
随后,胡林翼被任命为湖北巡抚,但号令仅及于长江以南州县,粮饷多被湖广总督杨霈截留。胡林翼在汉阳集中兵力,准备一战,结果大本营被太平军攻占。他羞愤至极,像曾国藩一样,欲单骑冲入敌阵赴死,被水师都司鲍超救下。战后,胡林翼整顿兵马,设局征收厘金,与当地官员搞好关系,总算打开了局面。正因他有巡抚一职,才不至于沦落到曾国藩的境地。
为收复武昌,胡林翼向曾国藩借来了罗泽南。曾国藩本不想借人。他手下两员大将,一个塔齐布,一个罗泽南。塔齐布于1855年8月病逝,罗泽南要是再离开,曾国藩便无人可用了。但罗泽南却另有想法,他给曾国藩写信道,只有解武昌之围,才能解江西之困。看似是战略上的分歧,但两人之间的嫌隙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大。

当年与曾国藩闹分裂的王錱就是罗泽南的弟子,两人因此闹得很僵。湘军出师之后,罗泽南立下大功,被授予浙江宁、绍、台道员一职。曾国藩为了战局考虑,不放罗泽南走。此后,罗泽南屡获大胜,堪称战功第一,但曾国藩从未保举过实职。清廷也有意漠视这一问题,只嘉奖,不给官职。更何况,曾国藩在江西举步维艰,面对石达开也没有什么胜利的机会。显然,罗泽南去胡林翼那边更有前途。
曾国藩又何尝不知罗泽南的心思,便主动送好友脱离苦海:“然计东南大局宜如此,今俱困江西无益。此军幸克武昌,天下大势犹可为,吾虽困犹荣也。”他上书清廷,要求将罗泽南调往湖北,只是留了一个后手:克复武汉后,立刻回援江西。
罗泽南进入湖北,攻无不克,轻松拔除了武昌外围的太平军据点。然而,江西的局势急转直下,石达开连战连捷、攻城略地,曾国藩只能坐守南昌一座孤城。1856年3月,胡林翼接到曾国藩求援信,他不好自己处置罗泽南部的去向,便让清廷做这个决定。清朝将皮球踢回胡林翼这边,让其酌情办理,最好速克武昌城,然后回师江西。如果胡林翼放弃大好局面,全力增援曾国藩,固然有利于湘军的团结,却会引起部下的不满;假若他顾及自身利益,不速援曾国藩,则湘军内部两大派系的矛盾必然加剧。
胡林翼与罗泽南都不愿意支援江西,但碍于私谊和上命,不得不对武昌城发动了强攻。攻城时,罗泽南左额被枪弹打中,不治身死。胡林翼从罗军中分四千人交给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驰援江西,又让李续宾统领罗军主力,改强攻为长期围困。而石达开听闻天京被围,回师进攻江南大营,曾国藩才稍微松口气。
1856年夏,石达开又引军驰援武昌,与胡林翼僵持近一个月。之后,天京事变发生,石达开撤走,湘军终于攻克了武昌。此后,胡林翼所部湘军日趋壮大,声望如日中天,其势头已经隐隐压过了曾国藩。
而曾国藩的进取心早被消磨地干干净净了。1857年2月,由于父亲去世,他返乡奔丧。这年,他上了一个折子,大意为:如果不能任巡抚,就不能管理官吏,管理不了官吏,就治不了军,哪怕能治军,也筹不了饷。——这实际上是伸手要权。
然而,朝廷无视了这一请求。年底,他的辞职信获批,他终于可以远离令人沮丧的战场和官场了。

3
1858年,湘军主力进攻安徽三河城,惨败。李续宾自杀,曾国华战死,六千精锐全军覆没。在此前后,曾国藩、胡林翼(因母亲去世守孝在家)重回军营。
胡林翼手下有三员悍将,一是多隆阿,一是鲍超,一是李续宾的弟弟李续宜。曾国藩可用之人,除了水师的杨载福、彭玉麟之外,就是他的弟弟——曾国荃。
1856年,吉安知府邀请时在长沙的曾国荃商议御敌之策。曾国荃招募湘勇3000人,骆秉章又送了一支3000人的部队,合6000人,组成“吉字营”。1858年,曾国荃攻克吉安,“吉字营”成为曾国藩手下最重要的人马。
重新出山后,曾国藩多了一些主见。朝廷一会调他去四川,一会让他去浙江,他都婉言拒绝、置之不理。如果任由那些坐居朝堂的大人们坏事,剿贼大业几时能休?
一直以来,清廷剿太平军之役,靠的是南京城外的绿营军队。1860年,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主帅张国梁战死,和春自杀,两江总督何桂清逃亡。就在东南各省群龙无首之际,曾国藩的时代终于到来了。
1860年6月,皇帝让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督办安徽、江西、江苏三省军务。曾国藩可以随意调用经费,设卡抽税,而不用再看绿营将领和地方官员的脸色了。1861年,清廷任命李续宜为安徽巡抚。1862年,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任命李鸿章为江苏巡抚。清廷通过给予湘军高级将领官职的办法,将他们一一纳入体制之中。但兵制却没有改动——湘系是崛起了,湘军仍悬浮于体制之外。
曾国藩很早就有一个战略构想。在他看来,南方作乱的叛军,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没有根据地的流寇,比如石达开;一种是建都称王的反贼,比如洪秀全。对付前者,只能坚壁清野,挫其锐气。对付后者,可以将其包围,先翦其枝叶,再直捣天京。江南大营的失败,就在于他们没有攻下南京以西的大城市,任其在长江驰骋。因此,曾国藩的首个目标是安庆。
1860年7月,曾国藩在皖南的祁门设立大营。此地四面环山,山势陡峭,仅一条官马道与外界连通,乃兵家险地。曾国藩却十分满意这个地方:“每一隘口,不过一哨,即可坚守,并无须多兵也。”
同时,经曾国藩保举,左宗棠得以襄办军务,招募“楚军”。左宗棠虽名满天下,但还是战场上的新人。他招募了5000人,进驻景德镇,拱卫祁门。
8月,曾国荃进抵安庆城下,在安庆的东、北、西三面开挖两道长壕,以围为攻。内壕用以围困安庆城内的太平军,外壕用以抵抗前来援救的太平军,城南的长江则由湘军水师负责巡逻。太平军人数远多于湘军,因此湘军要尽量避免野战,诱使敌方来攻。
太平军惯用的策略是围魏救赵。安庆城内物资还算充足,兵力也足够,坚守不成问题。于是,太平军派遣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分头进击,直取防守薄弱的武昌。一旦拿下武昌,湘军就如同瓮中之鳖;而湘军若是急于回援,围攻安庆的曾国荃部就会陷入危险之中。
英王陈玉成刚过桐城,就遇到了多隆阿率领的两万骑兵。太平军不敌,退守桐城,等到冬天过去,便向武昌飞奔而去。
忠王李秀成部则出现在了祁门附近。先是侍王李世贤率军拿下休宁镇,距离曾国藩仅50公里。之后李秀成的主力发动奇袭,祁门周边的据点一一失守。曾国藩没料到太平军竟能在浓雾和大雪天气杀来,心急如焚。12月18日,曾国藩知建德不守,“竟夕不能成寐”。24日,大营粮道断绝,许多部队无米可炊。30日,太平军就在十里之外了。
他给曾国荃写信,平淡地交代遗言,然后等待着屠刀落下。幸好,李秀成的注意力并不在祁门,只是试探一下虚实。随后鲍超带着“霆军”杀到,与李秀成激战了一番。李秀成见占不到便宜,绕道往江西去了。
对于曾国藩来说,这个冬天实在太漫长了。
李秀成走后,干王洪仁玕、辅王杨辅清与李世贤等聚集于休宁、婺源等处。左宗棠在景德镇的楚军,势单力薄;祁门这边的防御,更是危如累卵。曾国藩时而失去与安庆的联系,时而担忧断绝的粮道,几乎每天都在孤注一掷,以搏得一线生机。1861年2月15日,太平军相继攻破大洪岭、大赤岭。次日,太平军逼近祁门县城,“文报不通者五日,饷道不通者二十余日”。3月12日,李世贤攻打祁门县城。24日,祁门大营被包抄。之后,景德镇失陷,曾国藩彻底陷入包围圈中。
4月11日,曾国藩集合兵力,进攻徽州,欲突破封锁。太平军乘机对祁门大营发起攻击。事已至此,曾国藩只能硬着头皮打下徽州,不可能回头。14日,战事不顺,曾国藩“心如火炙,殆不知生之可乐,死之可悲矣”。21日,太平军放火偷袭营盘,湘军溃败。曾国藩退回祁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他再次写下遗书,告诫儿子们不要从军,不要当官,剿匪事业毁了他的一生,现在想来,只有读圣贤书的时候,心里才是真正快乐的吧。恰在此时,左宗棠在景德镇打了一场翻身仗,大败太平军,威胁其后路,使得太平军必须撤下重围。
曾国藩又又又又活了下来。
当祁门陷入危急之时,北京同样正经历一场劫难。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皇帝出逃,圆明园被焚。此时,朝廷命令曾国藩派遣鲍超的霆军前赴“勤王”。曾国藩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纠结之中。若不派军,坐视皇帝蒙难,忠君爱国之大义从何谈起?若派军,祁门必定失守,安庆之围不攻自破。两难之下,曾国藩采用拖字诀。他上折称,鲍超赶到京城需三个月,缓不济急,不如从诸将(包括曾国藩本人)中挑选一人,带兵北上勤王。这折子未送到北京,朝廷就已经议和了。
霆军不用北上的消息传来,曾国藩也不知该高兴还是难过。这世上,比他更厌恶外国人的人恐怕不多。他看着新签订的条约,“不觉呜咽,比之五胡乱华,气象更为难堪”。
整个世界都在分崩离析,坚守在祁门这小小一隅,究竟有何意义?但或许正是这天倾地覆的景象,才让曾国藩倾其所有。他对弟弟说:“普天下处处皆系贼占上风,独安庆一城系贼占下风,岂肯轻易撤退?”命运的玩弄,反而成为他坚持下去的理由。
全天下只有江南还没有分出胜负,只要他不放弃,儒家就不会输,天下就不会亡。
4
在武昌,胡林翼同样陷入了焦虑之中。
1861年,陈玉成轻取黄州,直逼武昌。湘军为了围安庆,将所有主力都派去了安徽,湖北境内防御空虚,“黄州以上无一兵一卒”。胡林翼手下只有一千余人,根本救不了武昌。可以说,安庆之围的战略构想简直是错漏百出,湘军的运气要是稍微差一点,全都要变成孤魂野鬼,难怪胡林翼说自己“笨人下棋,死不顾家”。
这时的胡林翼已患肺病好几个月了,自身性命难保,对于东南大局心有余而力不足。恰巧,一个英国人出面了。
英国外交官巴夏礼找到了陈玉成,警告他不要进攻汉口,因为汉口是《北京条约》里规定的通商口岸,涉及大英的利益。当时,在洪仁玕的建议下,太平天国打算和列强建立良好关系,以求得枪炮舰船。而且,安庆城内的太平军正得到英国船的救济,湘军水师虽封锁江面,却不敢对往来的英国船只开炮。陈玉成见是英国人,不敢怠慢,将自己围魏救赵的计划通盘说出,并说自己正在考虑要不要打汉阳。巴夏礼强硬地说道,太平军若拿下武汉三城中任何一城,必然会破坏整个商业中心的贸易。

陈玉成拿不定主意,派人回南京听取指示,自己则在武昌城外徘徊,等待着李秀成的到来。李秀成从祁门离开之后,悠闲地跑到江西扩军去了,待他姗姗来迟,陈玉成已经撤走了。时间拖得越久,越对太平军不利。此时,湖北各地已经构筑了防线,李续宜、鲍超的部队也正在赶来。稍有不慎,太平军就陷入包围圈之中。这个时候开战,胜算不大。于是,李秀成待了没多久,就回江浙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去了。
胜利的天平迅速倒向了湘军。
陈玉成进军集贤关,设了四座营垒,又在安庆城北菱湖两侧另筑十八座营垒,与安庆城取得了联系。陈玉成猛攻安庆围军三天,未能突破由高垒深壕构成的主要防御工事,而多隆阿又将其反包围住。随后,洪仁玕带兵赶到桐城,与多隆阿的骑兵对峙。安庆城外,已经不知围了多少圈军队了。
陈玉成决定接应援军,与洪仁玕一起夹击多隆阿。他留下12000人守卫集贤关和菱湖两侧的营垒,率领剩余部队北上。但计划外泄,多隆阿派一支骑兵绕到陈玉成背后偷袭,将其击溃,迫使他逃往桐城。那12000人瞬间陷入绝境,没有任何城墙的守护。
鲍超的霆军杀至,设立炮台,对着集贤关的四座营垒猛轰了一个礼拜。之后,鲍超派人去劝降,其中有三个垒,大约三千人左右放弃了抵抗。鲍超举起屠刀,将这些人全都杀光。第四座营垒血战到底,还是被攻下,所有人被屠杀,只留下一个活口——主将刘玱林。鲍超将其押到安庆城下,活活肢解,让城内守军明白反抗的下场。
另一边,曾国荃也在围剿菱湖两侧的营垒。这些营垒兵力更多,撑了更久,最终粮草用尽,逃往城里。湘军一路截杀,拿下菱湖,完成对安庆城的全面合围。
曾国荃不是天性嗜杀之人,见多了鲜血,也会良心不安。曾国藩则完全没有这种顾虑,因为他不把“无父无君”的太平军当人看。他劝告弟弟,即便孔子复生,也会说杀的没错。有时,他恼火于弟弟的“仁慈”,言辞激烈地说道:“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

1861年5月5日,曾国藩离开祁门这一险地,将大营搬到了东流。他看出安庆城的脖子上已紧紧套上绞索,只需要坚持下去就行。
8月,陈玉成向安庆围军发动疯狂的攻击,城内的守军也大举冲出,试图打通一条路。他已经没有办法了,只能采用这种自杀式的人海战术。湘军撑过了太平军的反扑,陈玉成彻底绝了救安庆的念头,撤军离去。
9月5日,湘军攻陷安庆。进城时,已无人防守。目之所及,只是两万多骨瘦如柴的饿鬼。此前,曾国藩给曾国荃写信道:“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弟意如何?”湘军虽获大胜,但情况并不乐观:欠薪欠饷已成普遍现象,士兵疲惫不堪,扩军之后军纪也差了很多。即便如此,相比于乌泱泱的太平军,人数还是太少。
即便这两万多人有不少是平民,曾国藩还是决定杀光他们,因为这是最便捷、最省事的办法。也有人说,湘军只杀了一万余人,掳走了剩下万余妇女。
1863年1月,曾国藩在其弟曾国葆死后,曾写过一副挽联:“大地干戈十二年,举室效愚忠,自称家国报恩子;诸兄离散三千里,音书寄涕泪,同哭天涯急难人。”哀痛之极,却绝无后悔之意。
人之性命,岂可与“道”相提并论?这就是曾国藩的信念和价值观。或许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坚守到底吧。
胡林翼在得知安庆之战的结果后不久,离开了人世。曾国藩成为南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只要他仍效忠于朝廷,清朝就会屹立不倒。新势力正在改变着这个王朝的权力格局,只是,大部分的新贵终将沦为时代的祭品。
参考文献:
【清】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传忠书局,光绪二年(1876年)
【清】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2012年
【清】胡林翼:《胡林翼集》,岳麓书社,2008年
【清】罗泽南:《罗泽南集》,岳麓书社,2010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96年
龙盛运:《湘军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
朱东安:《曾国藩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谭伯牛:《天京之围》,天地出版社,2025年
通弘网配资-通弘网配资官网-期货配资查询-可查配资实盘平台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